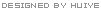中国地质和教育工作者,本社中央委员丁道衡同志和我们永别了。在重庆公祭之日,他的同志、同事和学生,都悲恸的落下泪来。我们远在北京的一些同志,也均有同样的哀恸!
我的哀恸,不仅由于他曾经是我的同志和事业上多年亲密的伙伴,而且想到:他在过去反动统治黑暗岁月里,学术上受过学阀丁文江辈的歧视与排斥,政治上受过蒋匪帮文化军事特务的欺凌与监禁。解放后,他始终站在国家指定的岗位上,满怀兴奋地执行着他所热爱的文教工作,并打算以更大的努力在学术研究上和教学改革工作上为祖国作出更多贡献。但是更重要的,他是一向被科学界、教育界公认为一位正直的科学工作者和优秀的社会活动家,同时又是九三学社一位优秀的社员和领导者。他的死,是中国地质学界、教育界和九三学社一项无可补偿的损失,也是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团糟中一项重大的损失!
我们对于这样一位同志只悲痛一番就算完了吗?不,应该是纪念他在政治、社会、学术和教育各方面优秀的活动与卓越的成就,把他未完成的事业继续担负起来,使我们的悼念心情和我们和他的共同事业、共同愿望相结合,才能对这次悼念有积极的意义。
一、 值得我们纪念的是他的优秀品质正直作风,以及对恶势力坚决斗争和对人民积极服务的精神
他虽然出生在封建地主家庭里,由于时代、环境、教育各项条件的影响,在他身上就产生和发展着小资产阶级的正义感,坚持正义和真理,敢于对恶势力坚决斗争。他缄默寡言,最反对吹牛拍马,在北大毕业以后,留校工作期间,遭受学阀丁文江的歧视和压迫。丁文江披着科学家的外衣,实际是一个典型买办,迷信外国资产阶级权威,看不起广大的青年,常说我的同姓没有经验决不可能在新疆有所成就。一九四八——四九年,西南各级学校不堪受反动政权压迫,屡次罢课,当时道衡同志在重庆大学教授会上公开痛斥蒋政权的黑暗混乱,又在贵州大学以上教授会主席的地位领导罢课,特务百般威吓,不为所动,终遭捕押,虽在缧之中,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了对人民敌人的斗争。
他重视集体利益和工作需要,坚决服从祖国分配,不避艰苦,能够以忘我精神从事劳动:早在一九二七——三O年,他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遍历内蒙、宁夏、甘肃直到新疆塔什库尔干,走过沙漠、穿过天山、不避一切艰苦坚持地质勘查工作,三年如一日。这种伟大精神,在今日青年地质工作者队伍中已经不是罕见的事,而在三十年前确实是难能可贵。他在新疆西部工作时并且和维吾尔塔吉克兄弟民族相处得非常亲密,学习他们的评议文字,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所以当他离开新疆西部的时候,五位维吾尔、塔吉克民族同胞自动地护送他到乌鲁木齐,也正因他能密切联系群众和团结兄弟民族,所以才能顺利地完成在新疆等地质工作。解放后,他原担任贵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五二年调任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他服从国家需要和自己热爱的专业,就衷心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当时他只身在重大工作,家属尚留在贵州,生活多有困难,但他全心全力地埋苦干,工作热情并不稍减。道衡同志早在贵大工作时期染有心脏病。去年初夏,更因工作过度,血压突升,卧病月余,血压稍降,就参加布置普查工作。此后,血压迄不正常。八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来京开会,会后应邀出席本社北京地质学院支社和地质部支社的座谈会报告参加大会的观感,出席全国地质院系教学大纲会议和本社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回渝以后,在重庆市协商会、重庆大学、本社重庆分社等处作了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传达报告,并积极进行了关于解放台湾的宣传。同时,对于他的岗位工作未尝一日稍懈,而他还常常自叹说:时代进步太快了,我跑得太慢了。
他对人处世坚持原则,不徇私情:重庆大学实行专业设置后,地质系按课程性质分设四个教研组。其中地质组的个别教师只从个人工作出发,曾力主把普通地质和构造地质分为两个教研室。这样做,不仅在工作上有许多困难,人力上也有很大损失。道衡同志为了整体利益,始终坚持原则,拒绝了老友的建议。
他虚心学习欢迎批评:他在业务、学术和思想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平,但他从不自高自大。解放后,他自觉地、积极地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更是不遗余力。大小报告无不准时到场听讲并作笔记。开会时和个别谈话时,如有人对他提出批评或对工作提出意见,无论正确与否,他也总要笔记下来,虚心反省和研究。他本是一个谨讷缄默的人,解放后,通过学习,勇于发言,对国家经济和文教建设,向领导上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
二、 学术上的成就
一九二七——三O年间他在内蒙到新疆地区考察,他是我国第一次在内蒙新疆进行地质勘查工作的地质工作者。他发现了内蒙大铁矿,并估计出它的矿量,这是中国最丰富的铁矿。他又在天山南部发现两个重要的西北——东南向大断层(现已为苏联专家证实),当时地质界学阀,迷信外国资产阶级权威,固执的认为内蒙不可能有很大铁矿的存在,也不相信天山的大断层,当时对这位青年地质学家辛勤劳动的科学发现,却主观地采取粗暴蔑视的态度把它束之高阁。只是在人民政权建立以后,科学工作受到重视,道衡同志当年就冤沉海底的科学发现才被重视起来。今天人民肯定了他的卓越成绩,接受他的成果,而且已使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了。其次,当年他在新疆完成塔什库尔干五十万分之一地质图以及其他一些原始科学材料,袁复礼教授已允代为整理和出版。一九三九年,他在参加川康科学考察团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中,研究过西南二叠纪岩中的铝矾土矿,确定了该矿层位及其远景估价。我国西南的铝矿研究工作,实际上是从道衡同志开始的。
一九三四年——三八年,他在德国的柏林大学从斯蒂来STILLE学构造,又到马堡大学从卫德钦德WEDEKIND学习地层古生物。在这个期间,他作了一些创造性的古生物研究工作,解决了古生海绵生物系统位置问题。在此以前,一般多认为属珊瑚,但从丁同志发现海绵骨针之后,才把多年来国际学术上一个久悬问题解决,他这篇论文曾引起世界学者的重视和争辩。嗣后,他又做了一系列的古生物研究,如枭头介的描述和有关珊瑚的研究等,深为中外地质人士所赞许。因此,卫德钦教授想留他担任讲师,但他坚决地回到祖国来,为的要在抗日民族战争中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他之所以有这些成就,是由于他对治学一贯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对丁文江等伪装科学的实验主义的斗争。他对古生物的研究,能抓住古生物基本构造中的主要牲和发展规律,能循着原物发展规律去进行仔细的分析和综合。他在德国从卫德钦教授学习很久、虽然卫氏是一位有名古生物学家,对他也很好,但他绝不迷信权威崇拜偶像,常常批评卫氏的治学方法——机械唯物论。去年九月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哲学和学术思想的严重斗争,道衡同志曾经说过,要对地质学界主观唯心派丁文江等的余毒进行批判和清算,并说要对卫氏的学术研究和工作进行批判。不久以前,他还和乐森寻同志谈到,自己已经准备了两个科学研究的专题:一个是答辩阿拉里齐和劳本菲斯教授否认古杯海绵的问题,一个是反驳马廷英教授误解卫氏提出的珊瑚隔壁锥的理论。孰料这些科学讨论都已成为未完成的遗志。我们痛失这样一位忠于科学研究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也痛失这样一位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斗争的先锋健将!
三、 教育工作上的贡献
他热爱教育工作,积极培养青年:道衡同志在教育界服务整整三十年。一九四二年任贵大工学院长以后,更是绝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工作。从任重大地质系主任以后,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培养训练地质干部方面。他认为青年一代最有希望,老年一代应反悔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他不但组织和推动全系教师面向教学,并且他自己还担任古生物学课程。对学生总是很细心的讲授和辅导,启发和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使他们成为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地质工作干部和地质科学研究者。一九上O至四二年他在嘉定任武汉大学矿冶系教授时,当时教师生活最苦,多数教师典当殆尽,被迫改业,但道衡同志始终坚持下来,不离开他的地质专业和教学岗位。当时他并未负行政责任,而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支持了一个系。他每早八时准时到系工作,下午就穿上他的白色工作服领导实习,一年中他担任过六门不同课程,并且工切实习还是在没有助教的情况下单独指导的。他不分星期、不管例假,整天整月地都在备课和工作。一九四五——四六年,他在贵大创办了地质系,自己也兼了许多课程,当时他是工学院长兼系主任,但他丝毫没有所谓学者架子,对同学和工友都很亲切和霭,只要他有功夫,不管什么工作他都肯去做。一九四三年,我因赴贵阳参加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届年会,会后返昆途中路过安顺。贵大工学院设在安顺旧藩台衙门,房子古老,而道衡同志在经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把它搞得相当整齐清洁,把阳光充足房间改为教室,基本上合于教学之用。我是夜间到的,看见他正在灯下一张极小办公桌上亲自动手写一件公告。一九四八——四九年他还每年以两个月时间到重大地质系兼职课,解决重大地质系老师缺乏的困难。
他能掌握政策,团结教师和新老关系:解放后他担任贵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西南文教委员会副主委,基本上完成了人民所赋予的任务,把旧的贵州大学改造成为新型学校,在团结文教科学工作者的工作上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后来贵大地质系并入重大地质系,调他任系主任,该系内教师的团结关系一向不够好,不能发挥应有力量,他就首先着手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不到一年工夫,就克服了过去不团结的现象,使教学工作基本上走入正轨。
他推动教学改革工作,不遗余力:从院系调整后,中央提出教学改革和学习苏联的号召以来,道衡同志首先以实际行动响应,带头学习,带头推行,而且始终不懈地贯彻下去,在他的岗位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九五二年,他在中央教育部召开的院系调整会议上被派为地质组的召集人之一,工作非常积极。在去年高教部和地质部召开的全国地质院系教学大纲修订会议上,他任地史和古生物学小组的组长,该组精心修订的教学大纲,获得北京地质学院苏联专家组长的好评,当时专家因苏联正在修订教学大纲,要把这一大纲草案送到苏联去参考。该组之所以获得这项成就,与道衡同志平日认真学习苏联、研究教学问题以及领导小组的劳绩,显然是分不开的。他逝世那天(二月二十一日)的上午,血压已相当的高,他仍坚持布置本年教学和生产实习工作,并且和系内教师详细讨论了学生毕业设计具体作法和步骤。他一向关怀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恢复,并建议北大会应从早培养地质测量、科学研究人才和师资。据我所知,领导上已经决定把他调来北大参加建系的工作,现在他的遗志只能由其他同志担负起来。
上面所说的不过是他对国家对人民的主要贡献和最值得我们效法的重大事迹。假若这篇文章能够对文教科学工作者同志、对本社同志、以及广大的表扬地质工作者们和对目前正在展开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批判在自然科学界有一点帮助的话,那就是我的唯一的愿望了。
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 版权所有
渝ICP备11003224号-1 公安机关备案号 50010302000123
Copyright www.cq93.gov.cn All Rights Reserved TEL:023-6384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