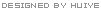天边,一颗流星划过
——记忆中的胡甫珊先生片断
郭 祥
与胡先生、冯克老交往,因缘统战宣传工作。1999年至2005年,我任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重庆统一战线》编辑部编辑。重庆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重要舞台,是政治协商,民盟、民建、九三学社、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四个民主党派的发祥地。按时任副部长、主编徐登全,宣传处处长、常务副主编李大刚的要求,统战政协文史稿件尤其要弄清史实、把握质量;要发挥统战联系广泛优势,与各界人士广交朋友、深交朋友,以扩大稿源。
为此,我有幸结识并拜访冯克熙、周永林、杨钟岫、唐弘仁、凌文远、胡甫珊、肖鸣锵等一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跃在重庆的老地下党、老报人,一段时间与他们定期座谈,就涉及文史稿件或他们的撰稿修改征询意见。冯老日常工作安排较满,胡先生因摔跤致股骨骨折,出院后完全靠扶滑椅挪动,相关稿件就直接约好,送到他们家中,当面征询意见、核对史实。
在我的印象中,作为解放前的老记者,胡先生非常知识、娴静、细心,治学非常严谨。她注意形象,不愿意以睡衣睡袍示来客,认为是不礼貌,发型从来一丝不乱。每次到她家中,多是听取冯克老意见。她家进门即餐厅,与客厅以一长廊隔开,为免去胡先生梳妆、穿衣着裤之苦,影响正常起居,起初冯克老和我就在餐桌上交换意见,胡先生有时就凑过来,招呼保姆续水,拿水果、糖果。后来熟悉,就改在了客厅,胡先生不时参加进来,静静地坐在一旁。看似无心,但有讹漏处,她会马上指出,进行补充。
有一次,我拿了一篇介绍“重庆名街”的文章请他们核审,其中谈到五四路,说是为了纪念“五四青年节”。胡先生当即指出:五四路过去是农村人进城卖鸡鸭等家禽的,叫鸡鸭街。
胡先生求实认真,钦佩之余是让我汗颜、感激。其实之前,我也一直以为五一路、八一路是纪念劳动节、建军节,五四路理所当然是纪念“五四青年节”。
那段时间,除约谈稿件,每逢春节、中秋,我都要陪市委统战部领导,或李大刚处长看望胡先生与冯克老。特别是少了领导“慰问”时,我们谈的课题更多、气氛更活跃一些。他们经常尽我们所需,互相补充,回忆往事。一次,冯克老风趣地说:说我是反革命,其实过去我们都是“胡家班”的人,是“中共走狗”。我们不解其意。
胡先生补充说:我们与胡子昂先生沾亲(侄女、侄女婿),当时都是新闻记者,是中国青年民主社(简称“青民社”,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在解放战争时期与胡子昂先生堂弟鹤霄(又名定一,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驻美公使、驻英大使),长子克林(中国青年民主社负责人、民盟盟员)、侄子甫臣(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工人报》副总编)、夏畦(万县民建会负责人)、北淇(中共党员,新闻记者),侄女胡珂(文艺工作者),被《新华时报》并称为“胡家班”,这其实是给胡子昂先生扣帽子的。《新华时报》是什么东西呢?国民党当局办的混淆《新华日报》、迷惑读者的反动报纸。
因为共同的追求,1946年,胡甫珊与冯克熙结为夫妇。结婚庆典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社会名流宾客300多人出席,被进步势力称为“展示民主力量的盛大婚礼”。从此,他俩心心相印、不离不弃,1999年、2000年分别被评为全国“金婚佳侣”、重庆市“恩爱夫妻”特别奖。话题曾经涉及到夫妇在“文革”期间的遭遇,胡先生风趣地说:1957年到1976年,克熙被关押、批斗,还“死不认罪”。组织上给我做工作,让我和他离婚。但我相信他的清白,宁可不要工作,也决不离婚。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原本是痛苦的回忆,她道来却非常轻松。她还解释:人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无论顺境逆境,是人生的宝贵财富,都会给人一些启示,值得珍视记忆。如果一味抱怨,那人活着就累了。这句话充满哲理,至今仿佛犹在耳边回荡。无论失意、彷徨,我总试着拾起对生活的感激,体会处处存在的人生乐趣。
她与冯克老有一对儿女。当时,儿子冯大卫留学美国后,在美国找到工作,女儿冯丹任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主任,外孙女和孙子分别就读美国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每次提到他们,他们总是非常高兴,话题更多一些。有一次还专门翻出他们的照片给我们看,言辞之间非常高兴、自豪。
胡先生家里的家俱都非常陈旧,但整体摆设整齐有序,环境一尘不染。重庆市曾为省部级领导修了一批别墅,分给冯克老一套,被他们婉拒。胡先生曾向我们解释,一是苦惯了,比起很多人,能够住现在这样的房子已非常知足了;二是时间长了,对这些家俱也非常有感情,如果再搬,要装修、添家俱,劳神费力。老了,也力不从心;三是别看我们一个曾担任副市长,享受行政副省部级、医疗正部级待遇,一个是离休干部,装修、添家俱,一下子花这么多钱,凑不出,也不忍心。
胡先生行走不便后,生活起居多由冯克老亲自呵护。冯克老身患绝症后,我们几次去探望、采访。那段时间,胡先生一看到我们,就像看到救星,不停向我们诉说:人都这样了,还照顾我,还不停工作。让他歇下来,他就是不听,真是让人着急哦。其情何堪,其意自明,让我们多劝劝冯克老。
冯克老去世十多天后,我与大刚处长专程看望胡先生,顺便拿去刊有我以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名义撰写的《斯人已去 风范长存》文章的《重庆日报》,以示纪念。这时的她神情已有些恍惚,扶着滑椅,默默地望着冯克老的遗像,眼泪长流不已,反复说:他身体比我好,却比我先走一步,都是我拖累了他呀!
其时,冯丹已赶回北京办理退休手续,大卫陪伴在侧。据大卫介绍,但有来熟人来看望慰问,妈妈都这么自责。美国公司一直在催他回去,妈妈也强调以工作为重,她有保姆照顾就行了。但这种情况如何放心。
2005年春节前夕,我与李大刚处长再次拜访胡先生。这时的她已昏然瘫痪在床,口辞不清。专门照顾她的冯丹轻轻告诉她:妈妈,统战部的人看您来了。立刻,几泣泪水从她的眼角渗出,嘴唇不停颤抖。那一刻,我非常心酸,想起曾经与冯克老、胡先生在一起,听他们风趣地谈古论今,想起她曾经那么勇敢坚强执着,“星”一般的辉煌人生……那一刻,我深深地为她祝福。
以后,我由宣传处调党派处,再不忍心打搅胡先生,以致只能从民盟、从朋友处或有音讯零星,而无由谋面。为找写作灵感,有时翻翻冯克老给我的赠书,自然就想起胡先生,常悯心于问,她还好么?
如今,有关于胡先生的一切似乎归于沉寂。天边,又一颗流星划过。此沉沉哀思布于心,聊以片断记忆、以拙文寄托。
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 版权所有
渝ICP备11003224号-1 公安机关备案号 50010302000123
Copyright www.cq93.gov.cn All Rights Reserved TEL:023-6384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