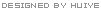1938年1月、2月,延安《解放》杂志分期刊载了康生《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一文,声称“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津贴。”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秉承王明旨意,也先后于3月发表了《关于陈独秀来信》等几篇短评,强调“陈独秀虽然声明了他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俘虏。”由王明、康生一手挑起的陈独秀“托派汉奸”一案由此引发。
陈独秀“托派汉奸”案起因
王明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成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长江局书记、党报委员会主席、《新华日报》董事会董事长。1937年11月,他与康生一伙从苏联回到延安,为什么不到2个月,就迫不及待地炮制这一冤案呢?
其一、王明、康生始终认为“托派是最危险的敌人”
历史上,陈独秀曾经是托派。大革命失败,他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曾在党内组织托派活动;在因故被开除党籍后,1929年12月,他与81人署名发表托陈取消派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与中共决裂,骂共产党为“匪”,“红军”为“寇”(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判刑入狱,仍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回忆)。1937年8月释放后,他拒绝托派要他回上海重整托派组织的要求,“道不同,不相为谋”,认为托派是“极左派的小集团”,“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
正在此时,经历苏共“反托”运动的王明一伙到了延安,得知中央与陈独秀联系合作抗日事宜,表示坚决反对。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责中央“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高。”,叫嚣“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其二、企图再次篡夺中共大权
对陈独秀,毛泽东倾向于他承认错误,到延安进一步教育帮助,使其认识改正错误后回到党内。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结束了长达4年之久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共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对此,王明一直心存不满。他回国后,一方面,对以“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为首中共中央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密切关注中央动向,伺机树立个人威信,企图再次篡夺中共中央大权。在获知毛泽东等与陈独秀联系合作抗日事宜,他大加鞭挞,并多次讲演或撰文,围绕陈是“托派汉奸”大做文章,主要矛头直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直到晚年,王明回忆:“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汉达成协议。由于我已回到延安,‘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这一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已准备同帝国主义反对派的积极帮凶——托派分子勾结起来。”
其三、与陈独秀存个人恩怨,借机打击报复
陈独秀在上海任中共总书记领导上海工人运动时,康生是上海总工会的一名干事,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恩怨和矛盾。但王明就不同了。1926年,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王明善于拉帮结派、投机钻营,他投靠副校长米夫,在米夫的安排下,担任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1927年年初,米夫率联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尚没毕业的王明担任翻译,并参加中共五大。这年6月,米夫带王明与陈独秀晤谈,对王大加吹捧,推荐他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陈对斯大林、共产国际不明中国国情,指手画脚早已心存不满,反感米夫的盛气凌人,对王明也没有好印象。他安排王明在中央宣传部任干事。对此,王明一直耿耿于怀。7月,由于大革命形势调诡,王明找借口随米夫又返回苏联,并向米夫告了陈一状。
此时羽翼丰满、野心勃勃的王明希望拉斯大林反托派大旗,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置陈独秀于死地,让他在党内、在全国人面前背上“托派汉奸”的骂名,以报一箭之仇。康生不过是王明“左倾”极端路线的追随者和策划者,他所说的:“1931年6、7月间,美国托匪格拉斯联合陈独秀等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的组织”,是别有用心的蓄意捏造。
张西曼等人对陈独秀的声援
时值抗战局势非常严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后,日寇侵略矛头直指武汉。大敌当前,由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1937年9月,陈独秀由南京抵武汉,曾先后在武汉大学、武昌华中大学、汉口青年会等处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呼吁抗日救亡。这样一个积极主张抗日、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中共直指是领取日本津帖、破坏抗战的汉奸,在武汉政界、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让很多人感到不解、不满,甚至不耻。
原《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曾在《报人生活杂忆》中回忆:“就连张西曼教授这样的靠近我党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都对这种武断的作法表示了不满。一些学者联名写信,要求澄清事实,王明不但不允许报纸发表这些信件,并且以评论的形式对此提出责难,伤害了这些朋友的感情。”
石忆所说张西曼时任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进步的社会活动家。1919年7月,他在北京大学与李大钊、陈独秀等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曾三次向孙中山建议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后曾参与创始九三学社。他是一个“平生只有主张正义,绝不计较利害(黄炎培评价)”,是非分明、敢作敢为之人。
该声明还在《武汉日报》同时刊发,被《扫荡报》、《血路》等转载,影响进一步扩大。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表示不赞成随意给陈独秀扣上汉奸帽子。
同期《新华日报》,林庚白发表声明,称“乃顷读该函”,“本人于该函之内容,完全不能同意,应不负任何责任!”对此,张西曼反应非常强烈,他在18日《新华日报》以“来函照登”形式强调:“我为什么敢负责为独秀先生辩护呢?就因为在他出狱后,作过数度的访问。”“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和对我所创中苏文化协会的伟大使命以及中苏两友邦联合肃清东方海盗的热烈期望中,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他还呼吁,“避免一切无谓摩擦和误会”,“痛定思痛,互相谅解,认清敌友,待罪图功。万不能稍存意气,重蹈以往覆辙,骨肉相残,殃民祸国。”
张西曼的言辞并不能打动王明、康生。
陈独秀在看到《新华日报》短评后,也给《新华日报》写信,非常悲愤地指出:“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新华日报》没有发表这封信,后几经周折改在《血路》、《武汉日报》和《扫荡报》上发表。
此时,罗汉又发表了一封致周恩来的公开信,叙述与叶剑英等接触“很融洽”,对王明、康生进行驳斥。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参与进来,对共产党发起围攻。
如果论争继续扩大化,无疑损害最大的是中共形象和抗日统一战线。按照中央指示,徐特立(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驻湘办事处代表)专程从长沙到武汉进行调解,表示歉意,这使陈独秀大为感动。周恩来还与多人交换意见,并派人拜访安慰陈独秀,希望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避免事态扩大。这样,这场风波暂时平息了下来。
《新华日报》围绕陈独秀是否是“托派汉奸”的所作所为,完全王明一手操纵。作为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毛泽东、张闻天等从未说陈独秀是“汉奸”,并强调“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只是忌惮于王明自称是共产国际、斯大林派来的,对于他有悖于中央与陈联合抗日精神的言行,中共中央暂时隐忍未发。但因为此事,陈独秀与中共永远决裂了,以后,骂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等等。
1939年1月,陈独秀寓居江津。6月,经张国焘建议,蒋介石命戴笠、胡宗南登门拜访,不情好意地拿出张西曼等9人在《大公报》公开信剪报,陈独秀仍气愤不已:“此诬陷之事,虽经徐特立先生调解,但我陈某的人身受到极大的攻击,至今仍未忘怀。”(郭 祥)
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 版权所有
渝ICP备11003224号-1 公安机关备案号 50010302000123
Copyright www.cq93.gov.cn All Rights Reserved TEL:023-6384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