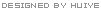我喜欢月,且无论阴晴圆缺。从有记忆起,近50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不同的环境、心境下,对月亮月光总有些不一样的记忆和感觉,有时还会萌生邂逅的感觉。任何时候,故乡江汉平原的月、童年的月始终承载着无忧无虑、我人生最美好的回忆。那时那月清澈骄艳,满是温馨清亮神秘的色彩,月光泼洒在地上,笼照着村庄、小桥、沟渠、庄稼地……柔和地勾勒出芸芸婆娑世界,挑动我幼稚好奇的心。当时大多家庭子女多,父母忙于生计,孩子都是散养,特别是男孩子,只要到点回家吃饭睡觉就行。有时吃宿他家,家长断不会刻意去寻。于是,月夜成就了我最跳皮、最惬意的回忆。夏月,我们吃完饭到河塘里扎几个猛子,便早早围坐在我堂伯父竹榻旁,听他讲瓦岗英雄传、薛仁贵征西、孙悟空闹天等故事,总百听不厌。伯父是一个以算命谋生的瞎子,记忆非常好,还能够用手工压面机为邻里做出一手好面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生产队打谷场码满了棉桔杆、堆放着稻草。月光下,我们在里面钻来钻去捉迷藏。有一次,一个小伙伴睡着了,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以为他已回家,便散去。他母亲以善骂闻于乡里,他半夜冻醒回家被责问:“死骷颅仔,为什么没死在外面。”这一节由他传出,让我们学他母亲的腔调,取笑他好久。冬春季节,我们做一些游戏驱寒。有一种叫“冲关”,两边按年龄胖瘦平分,这边排纵队齐喊:“天上玉皇大,地下阎王大,地上我最大。我放马了!”相隔3、4米的对方横队,中间两人手拉手横在前面,齐说“好了”。这边就猛冲过去,冲不过,冲关的归对方所有,冲过了,就点1名对方的归己方,一方只剩下2名算输。有时也与女孩混合玩老鹰捉鸡、跳绳等。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月的遐思与期待慢慢淡去,但也不乏几次对月色的震撼。1988年9月的一天,我执行军务到麻栗坡县。傍晚,应我一再恳求,一位祈姓老乡陪我去麻栗坡烈士陵园散步。陵园已初具规模,里面安息着900多名英烈,据小祈介绍,烈士中最大的30几岁,最小的16岁,平均年龄估计也就20来岁。烈士陵园离县城不远,大约半小时就到了。天已擦黑,只隐约排排白影,唯一清晰就是我们细细的脚步声。不经意间,一轮半月缓缓升起,月光煞白惨淡、毫无生气,渐渐笼罩陵园,显现竦峙静立、横竖有如军阵的一座座墓碑。我走走停停,不时抚摸碑体。碑林之中,我选择一处台阶坐下,默默体会陵园独有的宁静与悲壮,思考生命的价值:他们有父母亲人,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但为了国家和民族尊严,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血洒南疆,成为烈士。如今拜顾,站在月光下的我与躺着地下的他们阴阳两隔,此情何堪、其情何忍!其实,没人想牺牲当烈士。有位歌星唱着“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而出名,当时我们听着特别刺耳。而现在听到,总止不住眼泪潸然而下。月光之下,陵园缟素,恍若白日。不远处,小祈手中的香烟幽然明灭。时间倏忽到了1996年5月底,我带着1名军士长小王押运一批军用物资由重庆赴乌鲁木齐,1个闷罐车拉着一些装有设备的木箱,3个平板车载几辆军车。押运是一件苦差,一般在春秋季节,每趟几天十几天不等,每停站最要紧的是洗漱、加开水,买方便面、矿泉水。彼时天气已近燥热,行李也就没带多少。列车经四川、陕西,进入陕西宝鸡地界,满目黄土高原韵味。入甘肃第一站是天水,再过兰州,沿途经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因为是第一次到血性雄浑大西北,结合中国西域两千多年的历史,莫不欣喜以为新奇异常。过金昌后,天色已黑,我独自睡在闷罐车厢里。小王除了吃饭,一直呆在一辆指挥车里。至半夜,我被生生冻醒,非常纳闷,这种季节怎么还会如此寒冷,于是拉开车门。那一瞬间,我被强烈震撼了——一轮明月孤悬层云不生的寂寂夜空,在洁白无暇、冷峻威严的月光映衬下,连绵雪山嵬巍起伏,积雪冰坂交错反射出幽幽蓝光、白光。那一刻我体会到的是静,是由秦时明月汉时关生就、与内地熟悉的“千山鸟飞绝”绝然不同的摄人心魄的寂静、孤独,是月光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凉,以致于列车单调的轰刺声被牢牢抑制。
以我的地理知识推测,此外应该是祁连山侧。历史与现实激烈冲撞,我仿佛看到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营帐篝火冉冉;西域副校尉陈汤挥剑布阵,一时间旌旗猎猎、战马嘶鸣、征夫林列、长矛森森,“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豪言在旷野激荡;张骞、班超、玄奘背负使命,一路西向,风餐露宿,羁马徐行,而理解最深的莫过于“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所透露强烈的悲怆、怨愤与无奈。寒风在罐车里冲撞肆虐,拥衾而至清晨,透过半掩车门,渐行渐远的雪山、冒着饮烟的村庄、穿着厚厚棉袄蹲在墙脚晒太阳的老者、呵着热气蹒局田间劳作的啬夫,有如历史的穿越、季节的反转忽闪而过。列车继续西行,进入新疆,第一站为柳园。此后,便是茫茫沙漠戈壁。白天,在炎炎烈日下,罐车铁皮吸足热量,肆无忌惮的辐射释放。瞅准临停,我忙不迭地转到平板车,躲在汽车的阴影下,烘烤与暴晒,两害只能取其利了。途中在铁道以北,总看到一大片湖区,水气氤氲蒸腾,间或有建筑浮现,但不管怎么走,相随相行,总是那么远。还碰到一次热风暴,由北而南,裹沙挟石形成巨大黄幔,如洪水一般瞬间吞没一切。列车剧烈摇晃,几乎要被掀翻。10多分钟后,一切又归于平静。由于沿途车站较少,没能及时补充开水,晚上只能就矿泉水嚼方便面,并打定主意,露宿平板车。天空清澈无垠,繁星点点初上。不经意间,在列车东南方向出现一小片红色区域,猜想应该是铁路养护工或是其他年轻人准备搞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但没有人头攒动的迹象。寂寞的我立即打足精神,饶有风趣地加以期待关注。不一会,红色区域弥漫开来,突然间一点腥红冒出,并慢慢放大,我这才真正意识到这是戈壁初月腾跃的前奏。有如早晨初升的太阳,只是少了霞光,四周黢黑死寂。随着月亮全然托出,列车、戈壁顿时被染成腥红一遍。毫不夸张,那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大最圆最红的月,似乎比以往所见大两到三倍,月光暗淡失芒,像是害羞的少女,又如血色的碧玉,尽显温柔奢华。半夜,奇冷,赶紧打开一辆车,裹衾缩进了驾驶室。列车单调地轰刺弹奏,一路西行。
作者:郭祥,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社重庆市委宣传处处长、重庆多党合作历史研究理事会副秘书长、重庆作协会员
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员会 版权所有
渝ICP备11003224号-1 公安机关备案号 50010302000123
Copyright www.cq93.gov.cn All Rights Reserved TEL:023-63846365